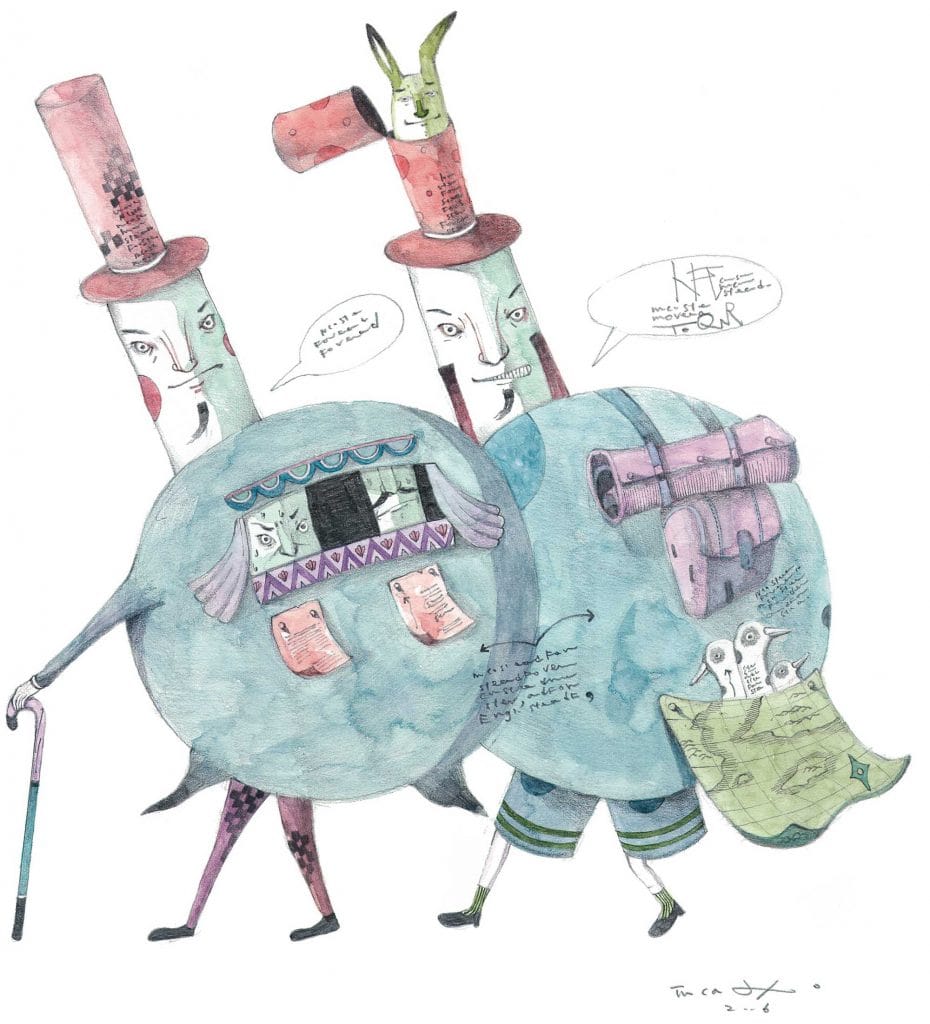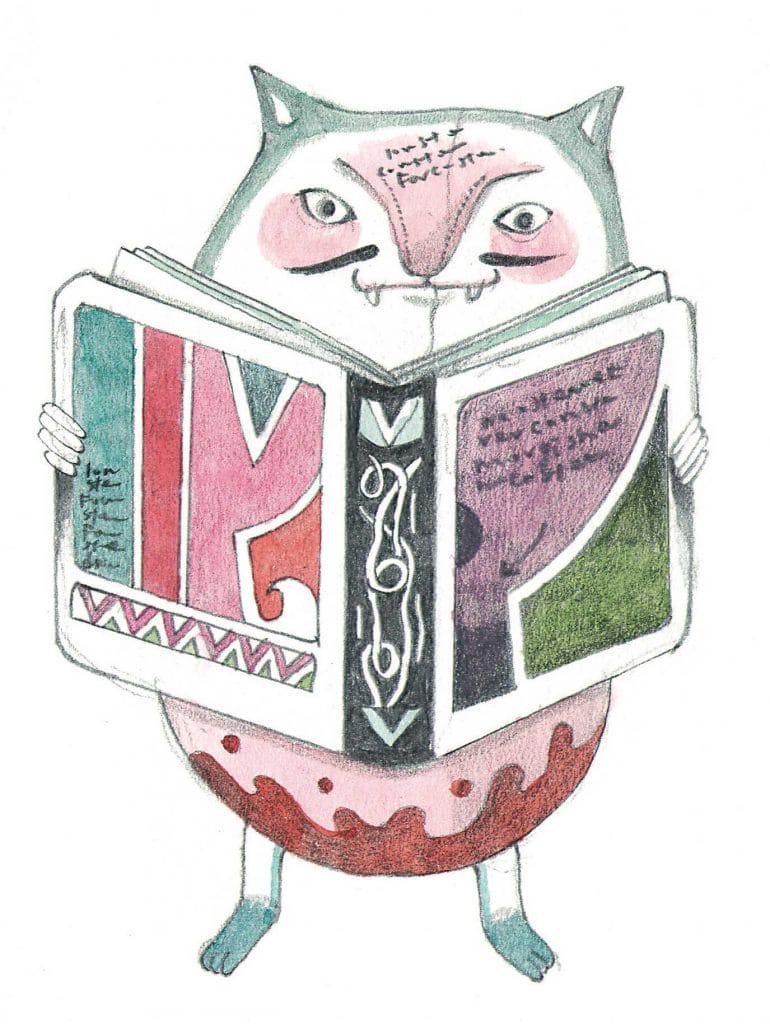莎士比亚的老妹妹们
在BBC当红影集《神探夏洛克》今年播出的最新一季,天外飞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原来夏洛克居然还有个妹妹尤若思,这妹妹不但比智商惊人的大哥二哥更聪明,还是操控人心的高手(不像两个性格乖戾、刻薄毒舌的哥哥一点也不得人缘),而部分由于这份异常的聪明,她最后沦落到一处戒备森严、俨然英国版恶魔岛监狱(Alcatraz)的精神病院,单独监禁,与世隔绝,永难再见天日……
看到这里,如果你是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或者像我一样有稿约在身,惦记着得写篇文章介绍安吉拉‧卡特充满莎剧典故的小说《明智的孩子》也许会想起另一个虚构的名人妹妹:茱蒂丝‧莎士比亚。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部如今已成经典的论述散文中,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威廉有个跟他一样才华洋溢、热爱戏剧、充满冒险精神的妹妹,就说叫茱蒂丝好了,在女人没有任何权利任何机会的十六世纪英格兰,她的一生可能是什么样子?
嗯,长话短说的答案是:会很惨,而且年纪轻轻就绝望自尽。[1] 当然,这两个天才妹妹的悲哀下场只是巧合,毕竟尤若思的问题出在反社会人格的癫狂和残酷,茱蒂丝的悲剧则是时代所致;虽然“发疯或自杀的秀异女子”此一典型在近代文学作品甚至现实人生中不幸屡见不鲜,但此一时彼一时,世界总是在进步,至少几百年之后的我们不用再面对社会体制与定见对女人才能、志向、乃至人生的局限和挤压了[2]
似乎不尽然。事实上,安吉拉‧卡特曾在接受访谈时提起自己的一个姑姑,个性活泼的她本可能去歌舞厅从事表演工作,却因歌舞女郎被视为不入流而无法如愿以偿,最后发疯死去。于是,卡特说,“那我就送她去歌舞厅好了。” [3] 于是,抑郁而终的姑姑在小说家笔下得到另一种人生,变成了《明智的孩子》中佻达奔放、敢爱敢恨、跳了将近七十年的舞依然老当益壮的欠思姊妹。
因为,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啊。
因为这是卡特,她可以浓郁、激烈、奇诡、华丽、张扬、既紫又黑(鲁西迪语),[4] 但绝不抑郁、悲情或控诉。在最后这本小说里,她更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欢快语调来讲述一个名符其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故事。
小说揭幕于某一个四月二十三日的早晨, [5] 结束在同一天的深夜——以时间范围而言倒是很符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不过当然,在一头一尾之间,叙事者朵拉‧欠思(“一身寒酸皮草、浓妆艳抹活像海报、蛇皮凉鞋里的脚趾甲涂成橘色、浑身酒气”[6]的资深公民兼前歌舞女郎)带我们回顾了她一生乃至整个家族高潮迭起又光怪陆离的历史。这天是莎士比亚的生日,[7] 是朵拉和双胞胎妹妹诺拉的七十五岁生日,也是她们“私生父”——封爵的国宝级莎剧演员梅齐尔‧罕择——和叔叔兼“甜心干爹”佩瑞格林‧罕择的百岁寿诞, [8] 对,这俩兄弟也是双胞胎。顺带一提,梅齐尔两度婚姻所出的四个子女都是双胞胎,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如果你觉得这里未免太多双胞胎、太多巧合,别忘了双胞胎和巧合可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两个重要元素,而亲爱的“老比尔”可是早从朵拉和诺拉的祖父母那一代起就与整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也是这整部作品最重要的背景、典故、与幽默或讽刺的来源。
关于莎士比亚,可以说的当然太多太多,也当然绝对不是这篇短短的介绍文字所能涵盖。以这本小说而言,一方面,莎剧本身就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但是各个人物曾参与演出的舞台剧或电影(此二者同时也是卡特喜爱且从事过的创作形式),亦在许多方面影响、呼应、甚至预言了他们的人生。另一方面,涉猎极广、文风多变、通晓法语德语、住过日本美国和澳洲的安吉拉‧卡特其实——说来也妙——是个非常英国的作家,[9] 而以莎剧为经、伦敦为纬的《明智的孩子》更是英国到了骨子里:除了藉由朵拉的回忆召唤昔日伦敦市民(尤其中下阶层一般小民)的生活细节,[10] 俯拾皆是的莎剧典故既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肌理和阅读乐趣,也可能形成复杂的文字迷宫和阅读挑战——而这,就端看你对莎翁作品的熟悉度了。
考虑到《明智的孩子》并不是一本学术论著——事实上,卡特刻意为叙事者朵拉选择了活力十足、荤腥不忌的俚俗口语,远离殿堂之上危乎高哉的阳春白雪——可能接触到的中文读者不见得熟悉莎士比亚,我在翻译过程中斟酌添加了一些注释,怎么说呢,也算出于一种“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心情吧。[11] 身为译者,若能藉由书页边缘的几行低声旁白,帮助更多读者掌握字里行间未曾明言的情节指涉或反差笑点,更能欣赏这部酣畅淋漓、光彩夺目、充满温暖笑声的小说(想到这是卡特辞世前最后一本作品,尤其令人惋惜唏嘘……),那就吾愿足矣。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重要的当然永远是小说本身。注意到了吗?我在这篇简介里几乎完全没提什么大纲情节精彩片段,因为那终究要等待每个读者自己去翻开书页,与书中的一切相遇啊。那么,回到文章一开始的脉络,假如莎士比亚有对双胞胎妹妹生在二十世纪初,是不受戏剧正统家族承认的私生女,成长过程中没爹没娘(但有自己建立的、虽无血缘关系却感情深厚的母系家庭),喜欢唱歌跳舞……她们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喔,可精彩的唷,打开这本书你就知道。唱歌跳舞是多开心的事!朵拉如是说。而我要说,读到好小说亦然。
脚注
- 欲知详情,不妨把《自己的房间》找来一读,这本书其实不厚,茱蒂丝出现在第三章。
- 尽管有时让人不期然想起夏宇〈Swing〉一诗中所言“口吃训练班或是/失语症治疗里那种令人心酸的/进步“。
- 《焚舟记‧别册》p.172。此处卡特小说译本页码皆以台版为准。
- 《焚舟记‧别册》p.8。
- 《明智的孩子》初版为1991年,我们不妨把小说叙事进行的那一天理解为1990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如此一来可推算欠思姊妹生于1915年,也符合书中提到她们出生在一次大战期间(p.49)、在1944年将满三十岁(p.123)。
- 《明智的孩子》pp.343-344。
- 现存资料一般将莎士比亚的生日纪录为他受洗的四月二十六日(1564年),四月二十三日则是他去世的日期(1616年),但在《明智的孩子》中卡特把后者当作莎翁生日。
- 关于欠思(Chance)和罕择(Hazard)这两个姓氏的翻译,我在《明智的孩子》中文版有以译注说明,基本上是在发音接近的前提之下同时希望传达英文原字“机缘巧合”、“不假思索”之意。
- 在《明智的孩子》和卡特的其他小说里,重要英国作家如狄更斯、奥斯丁、王尔德、卡罗尔、华兹华斯……等文学传统的影响都有或隐或显的一再展现。
- 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非英国读者如你我,欠思姊妹成长的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伦敦显然遥远陌生,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物偏偏总让我印象深刻——有点像罗兰‧巴特说的“刺点”(punctum)——比方皮卡地里广场有着白色地砖和小老太太收钱的投币公厕(pp.91-92);比方此书中数次作为背景被提及、卡特并曾另以短篇小说特别写过的panto(这种有着古老根源的奇妙剧种如今依然健在,我在英国念书时看过一两次,完全闹不明白);又比方卡特形容“大得车轮似的、让你满手金属臭味的棕色便士”(p.119)——还有比那个非十进位制、从1707年居然一口气用到1971年才改变、除了英国人没人搞得懂的镑和先令和便士系统更英国的东西吗?
- 此书的译注数量已经多到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的地步,其中一大部分与莎剧直接相关(不过这该“怪”卡特对吧),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很明显地击中了”(”a palpable hit”)一语典出《哈姆雷特》,但翻成中文后看来并无特殊之处,只是整个句子的一部分,若不加说明,就难免辜负卡特两度引用(第一章p.71,第五章p.320)的用心了。
文章内容可通过“创作共享”版权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使用传播
撰稿人: 严韵
严韵,资深读者,叛逃译者。译作四十余,曾数度获选中时开卷、诚品好读等年度好书。喜欢动物、旅行,有时打电动,有时写诗。